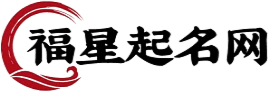免费起名,添加微信:000000 备注:起名!
周姓男孩取名独特一点(周姓男孩取名属虎)
我是你照拂的梦
你是 岁月长河
我是仰望者
你是 我之所来
也是我心之所归
我愿活成你的愿
走你所走的长路
写你未写的诗篇
愿不枉啊
愿勇往啊
……
父爱深深 悠悠长河
苏芊红
父亲生于1937年9月27日,那时为了战争需要,国民党时常抓壮丁,某一天我的三爷爷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为了躲避,我的爷爷常年不在家,去内蒙古一带替人放牧骆驼,家里的情形通常是只有父亲和二叔两个小孩,三个小脚女人:高祖母、曾祖母和祖母。父亲从八岁起靠做小买卖养活一家人。
父亲只上了小学一年级,就因为家里困难失学了,开始端个盘子学着做点小生意,杏子黄的时候就去附近农家买一些杏子,端到学校门口卖,也可以交换,地主家条件好的用白馍换,条件差点的用黑馍换,换完了再去挖点野菜,回家后奶奶煮成汤,放点盐巴,泡着或黑或白的馍,一家人充饥。穿的鞋经常是后跟部磨出一个大洞,走路石子垫脚,就给鞋里面垫个鞋垫,走着走着鞋垫就会从破洞里漏出来,就放下东西,把鞋垫塞回去,继续走路,等到桃子下来的时候了,也这样将就着过生活,毕竟时令水果季节很短,经常会有青黄不接,断顿的时候,忍饥挨饿是常态,饥饿令人心生恐惧。
父亲说他喜欢的还是秋天,比如苹果存放的时间长,还有土豆,存放的时间也长,令他记忆深刻的是某一个秋天,当时西市口有一个冯家店,开客栈的冯大爷,不知道从哪里进来了一批土豆,是那种小而黑的品种,煮熟后皮黑里黄,吃起来柔津津的有一股糯香味。八岁的父亲每天早上去买一盘,大概7~8斤的样子,端回来,由奶奶煮熟后,端出去卖了,能赚2毛钱,一毛钱可以买半块煤,另一毛钱可以买半蛊米,拿回家让奶奶做饭,下午再去端一盘土豆……如此循环往复,卖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一家人没有挨饿。中间有一个插曲,有人看到父亲的土豆卖得特别好,找到了冯大爷,要多出几分钱,把土豆全部买走,冯大爷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并说,“这个娃娃父亲长年不在家,一家人没吃没喝的,我惜可怜,把土豆留给他养家糊口,你就是多出一倍的价格我也不能卖给你。”
2017年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里,看到的名画《》:局促的空间,昏暗的灯光,狭窄的餐桌,桌上唯一的食物就是黑黑的土豆,每一个人眼中都流露着饥渴,生活的重压剥夺了他们全部的生趣。那一刻,我觉得人类的悲欢是相通的,至少穷人之间是。我在想,梵高要是遇到了冯大爷,一定会为他画一幅肖像的,因为冯大爷顾贫惜怜的善良与梵高的社会道德感高度相通。更何况,父亲说这个冯大爷长的一双剑眉,气宇轩昂,一表人才!
有一年过年了,家里只有几尺蓝布,父亲就让奶奶给二叔做了新衣服,他自己没有,出门去买了一包煮蓝(一种给布料染色的颜料),把满是布丁的,洗得发白的破衣服染成深蓝色,使其看起来新一点。
还有一年他说曾祖母去世了,古话说“死者为大”,父亲说他一个半大子娃娃,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只知道跪地嚎啕大哭,隔壁的王爷爷好心,带领穿着白色孝衫、腰里扎着麻绳的父亲,一家家跪求帮助……这个镜头在以前演穷人的电影里常有,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忙下,终于使亡者入土为安了。
等到父亲长到12岁的时候,就可以顶一个劳动力了,他就和大人们一道去十里墩担沙子,很累很辛苦,好处是工钱当天结算,虽不过几毛钱,但刚好够一家人当天的伙食,所以,父亲一点都不敢怠慢,每天早早地去,风雨无阻。有一天看砂场的人通知大家,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一天,但是,第二天一早,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天蒙蒙亮就出发了,到了沙窝就匆忙干活,一会会就担了十几趟,等看沙场的人来了,看见一座小山似的沙堆,吃了一惊,说道:“你这个娃娃,不是通知了今天放假一天吗?你怎么一个人来,这附近总有狼出没,大人们都是几个人约着一起来,你一个半大子娃娃多危险呐!”父亲说:“我知道今天放假,可是家里有几张嘴等着吃饭呢,我要是休息了,她们就该挨饿了……”。就在他们一问一答的过程中,从不远处的沙堆的后面走出了一头狼,显然他们的谈话惊扰了它,但它却没有理睬他们,径直沿着山根走了,留下了父亲和看沙场的人站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父亲说,他本打算去稍远一点的山上砍柴的,那一天没敢去。就近胡乱拾了一点就回家了,走在路上双腿发软。
显然这是一个孤独而富于人性的狼,带着苍凉的英雄色彩,它没有在那个饥饿年代攻击一个无助的半大孩子,致使他小脚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连同小脚的祖母陷入困境,因而比那个年代富于狼性的人或者这个年代主张狼性的人更加值得尊敬。
父亲说还有一段艰难的时期,实在找不到谋食的渠道,就去砖窑里背砖,每天空着肚子,从天麻麻亮一直背到满天星星,累病了,胸口疼,吐血,整个人虚脱了,蜡黄蜡黄的……邻居候岚萍的母亲看见了,掩着眼睛不敢再看第二眼,逢人就说,可怜的,这个娃娃活不成了。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命运的不确定性,有时是一段话开启的,尽管那句话有时候荒唐得像个笑话,也有可能说这话的还是一个老太太,更为蹊跷的是,多年以后,我的高中同学言之凿凿地说,说这句话的就是她奶奶,一个很精明很会走上级路线的吴姓老太太。我听了更惊叹命运的诡异叵测,瞬时变幻。多少人因为这句看似玩笑的话改变了命运的轨迹呀?
或许是这句话的因素,政府大面积地动员城市里的人去农村,俗称“上山下乡”运动,我的爷爷在漂泊了大半生之后回来了,他是积极的响应者,也是力行者,在去了一趟我们后来下乡的村子回来之后,坚定地要带着一家人去,说那里的土豆‘大得很’,即便是遇到了灾荒年,一个大土豆就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绝对不会再挨饿。经历过1960年大饥荒的人,知道饥饿是最大的敌人。于是,带着一家人浩浩荡荡出发了,刚去没地方住,住在人家废弃的地应子里,母亲说,不敢抬头,一抬头就会碰到窑洞顶,时不时会被掉下来的土迷了眼睛。
下乡的第二年,母亲就病倒了,得了,当时我不到一岁的样子,尚在襁褓之中,所以,父亲送母亲去看病,母亲怀里抱着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母亲病情有所好转,而这一个月父亲一边照料病重的母亲,一边照料我,据母亲说,由于照顾病人父亲每天早上起得很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我喂饱,一大碗糖水泡馍,等到9点多又喂一顿,一天吃四五顿,很快长得又白又胖,也学会了走路,总是在大人不注意的时候,眨巴眨巴地跑到别的病房里去,医生看到了就说,还是把孩子送回去吧,医院里病人这么多,万一传染个病咋办,父母一商量,决定把我送回去。我们下乡的那个小村子,距离县城有60里山路,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交通工具,家里有个自行车的就算条件好的,我们家穷,是没有的,实在没办法,只能徒步,父亲说一大早,他裹了件黄棉大衣,背着我就出发了,走了整整一天,中间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雪,路上很湿滑,走走停停,渴了,路过村庄,讨口水喝,到达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村庄里升起袅袅炊烟……走的时候又背走了我的三姐,一是她大点,会听话了,二是她从小体弱多病,父亲想着像喂我一样,把她喂胖点,身体好起来,有个小病小灾的能扛过去。
在下乡的村庄里,有一年兴修水利工程,应该是1976年,发生了大地震,我记得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在防地震,屋里不敢睡,在院里用木棍树枝搭了帐篷,我记得每晚母亲都会凄凄惶惶地说,你爸爸在山沟里搞水利,住在土窑里,要是一地震,土山就把人活埋了……这一年父亲一直在兴修水利,很少在家,母亲想着今年应该收入会好一点,搞副业受的苦大,给的多,结果,年终结算下来,给分了0.22元,也就是二角二分钱,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就是这么多,后来,看宋育红先生写的《我的青春我的塬》,关于如何计算年终收入的公式,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式,我的没有文化的父亲是怎么也算不出来的,其实也轮不到他计算,母亲只会用失望至极的口气叹息着说,到底是咋算的,你也不去问问,到底是咋算的?我的老实的父亲终究没有敢去问,他对有权力者是极其畏惧的,因为同样下乡的沈华玉一家,他父亲在队里看碾麦子的场地,白天生产队麦场上打碾好的麦子,晚上队长家人拉着去偷,他父亲极力看护,被打折了腰,成了残废,有一天听说公社大门口贴了大字报,我们几个小孩子好奇心大,跑了10里路去看,果然,白纸黑字,触目惊心,尽管错别字满片,文词不通,但大意是写清楚了,他父亲被打得很惨,卧床不起了,希望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后来怎么样了不得而知。但那个大字报描述的惨状触目惊心,令我心生恐惧,深刻的烙印还在我幼年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逆来顺受,干最苦最累的活,分最差的粮食,还被克扣,就因为我们是外来户,势单力薄。所以我的父母总觉得家里只有大弟弟一个男孩子,一来人丁单薄,二来劳动力不够,想再生一个男孩,结果,大弟弟下面又生了我四个妹妹,最后一个才是小弟,于是就有了我们姊妹十个,因为父母从不吵架,我们姊妹十个也从不吵架,和睦相处,从来都是大的帮助小的,小的爱护大的。
可眼前的困境咋度过呢,商量了一夜,最终还是父亲去城里求助舅舅家,那个年代都不宽裕,舅妈家也有5个孩子,但还是竭尽全力,把备的年货分了一半给我们。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在下乡的村子里,父亲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把我的五妹送给别人家,母亲有一个一起当过工人的小姐妹,结婚几年一直没有生小孩,一次在县城偶遇见到母亲又怀了第六个小孩,就说,这次要是闺女就送给我吧?当时我们在乡下。父亲就想着她们家在县城,旁边有,有水有蔬菜,日子能比我们下乡的干旱的山村好过一些,就点头答应了,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痛,总说这是此生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在农村最苦的事情就是拔麦子,上次看到张巨峰写的《拔麦子》真是感同身受啊。拔麦子是农村人说的“四大累”之一,夏日炎炎,尘土飞扬,三折子窝在地里,手脚并用,一天劳作下来体力和水分消耗巨大,不及时补充能量和水分,一定会中暑和虚脱的,所以拔麦子必须要带足干粮和水,特别是水更要带足带够。小孩子就只能去接趟,我也干过,就是帮大人拔麦子的,叫做“接趟”,就是沿着大人要拔的四行麦子,向前跑十多米后开始拔,小孩子个头小力气小不能像大人那样蹲在地上左右开弓地拔,只能站在地上,双手抓住麦秆用劲向上拔,每当大人拔到我“接趟”的地方,我也能拔两三米的长度, 这样大人就可以站起来伸伸腰,舒展一下筋骨,喝口水缓一下。“接趟”是不挣工分的,但能给大人省点力气。拔麦后的第二天全身的酸痛,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感觉身上的每个关节、每块肌肉、每寸皮肤都疼,再加上强烈的紫外线以及拔麦子带起的尘土混合着汗水黏在身上,麦芒刺在胳臂上,脸上隐隐作疼。通常第一天我会怀着好奇心去,第二天就会偷懒不去了。母亲说刚去农村时被村里人嘲笑“看把你个油饼皮皮剥掉不”。意思是城里人吃不了苦,会适时逃走,但我看到父亲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孩子们,每一年每一天都在咬着牙坚持着。
斯文?赫定发现之后,也发现了很多写有中文的书信,考古专家能够看懂书信的内容:“但当地政权面对悬在城头的阴云,从未对国家的责任有所退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当危险来临,他们没有分心,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工作,我怀着崇敬与情感读着中国人履行自己职责的品格与勇气。我们也由此理解了这个非凡的民族是如何把亚洲深深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我想我的父亲身上正是有着这样坚韧无畏的品质。
当然古人用无数诗词描述着田园美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在拔麦子的时候是体验不到的。更别说赫尔德林诗歌中可以遐想的诗意——“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大地上。”感觉到的只是土地更像一团生冷的压力,物理性地阻碍着你通向自由之路,写意中绝对精神自由不可能在土地这种现实性中自显。看似热烈的生产运动中焕发着噬人的冷血。那不厌其烦地作业,不断索讨着你心性的恒耐。土地和人一样都在莫名的烦躁和不可预计的未来性中争取着可以出逃的方式。无尽的劳作变成了日益折损和消耗精神生命的物理负担。土地似乎永远只是谋生苟活的手段,而不是可以安顿灵魂的家园。
2005年,我们带着父亲母亲去昆明旅行,伴着夜晚火车的卡塔声和路边忽明忽暗的灯光,父亲讲述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往事,讲了我小时候背着我走过的那60里山路,又讲了大姐小时候发高烧,痰迷症,人已经憋青了,他放下水果担子,抱起就往医院跑,到医院,有经验的医生马上嘴对嘴吸出一口浓痰,才哇地一声哭出来,医生说晚来一步,娃就没命了。二姐小时候,刚刚断奶,不吃奶粉,饿得皮包骨头,嘴里全是溃疡,疼的哭闹不止,拉出来的全是绿水水,抱着她到别人家去转转,看到人家孩子喝炼乳,要了一点试了试,炼乳又香又甜,二姐愿意喝,父亲高兴坏了,赶紧买了4大罐,高兴地抱回来。掏光了身上带的所有的钱,也是他做小买卖的所有本钱。三姐小时候有一次走丢了,上的红卫兵用喇叭喊着谁家孩子丢了,并描述了小女孩的穿戴,在鼓楼底下卖水果的父亲听到了,也顾不上自己的水果摊了,赶紧跑上去一看,果然是我的三姐。每一个孩子长大,都有惊心动魄的经历……每一个孩子小时候的事,他都记得,有些细节比母亲都记得清楚。父亲有十个孩子,从不打骂过任何一个,对每一个都很疼爱,小时候,只要母亲生气打孩子,他就不吃饭,摔下筷子就走。
父亲说,要不是这次旅行,我们父女怎么会有机会说这么多话呢?的确,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特别忙。
下乡返城,没有工作,买卖水果,舅舅从王美武家借了30元本钱开始,第一天拉不下面子。空手而归,第二天开始想着过河去看看,三滩糜滩有很多果树,就挑着两个大竹筐子,一路吆喝着收果子了,收了180斤苹果,挑着走十几里路,走到河边坐上渡到河对岸,再挑着担子走上十几里路到钟鼓楼底下,每天一趟,从不间断。所以,父亲的肩膀一个高一个低,走路时很明显,就是当年担水果担子造成的。钟鼓楼是我们靖远的中心地段,商贸中心,历史悠久,逢年过节人们都喜欢聚集在这里。所以父亲卖水果通常都在这里,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烈日暴晒,父亲坚守在这里十年如一日……
无数个冬日的夜晚,当我们在温暖的被窝睡得正酣时候,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响起来,常常是夜里12点或者更晚一些的凌晨了,他每次都坚持着把最后一点水果卖完,才肯回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为啥一定要卖完?留着我们吃不就好了么,父亲半天没吭声,晚上母亲悄悄给我说,每次剩的那些水果,就是一天的利润,要用这点利润来买米买面,养活我们一家大大小小十三张嘴。
等大了,读到《晋书?惠帝纪》,说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吃树皮,许多百姓被活活饿死,消息被报到了宫中,晋惠帝大为不解。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看到那个昏聩痴玩的晋惠帝,联想到自己,我羞愧难当,真是少不更事啊。
那些年父亲是铁人,全年无休,不敢生病,不曾在家里吃过一顿热饭。
有一次拉菜,不小心胳膊脱臼了,忍着剧痛回到家里父亲不停地说,这可咋办呢?胳膊不好可咋办呢?明天怎么去拉菜呢?我这一家人咋生活呢?那种凄然、绝望、无助……还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晚家里愁云惨淡,夜静了,我听着父亲粗重的呻吟声和弟弟妹妹们均匀的呼吸声,把头埋在被子里咬着被角,无声地流泪,天亮的时候听着父亲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突然嘎嘣一声,脱了臼的胳膊自动还上了卯,只听父亲一阵惊喜:好了好了,我的胳膊好了,老大老二快起来,拉菜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天晚上的情景,历历在目,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绝望,那种无可奈何,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父亲第一时间让我们几个失学的孩子去读书。1985年有了一点积蓄之后,买了三分地,盖了几间房子,返城七年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生意一步步好起来的时候,租了铺面,做百货批发,才不用每天站在寒风中,曝在烈日下谋生。
由于我们家距离二中比较近,我们都上学出来后,家里有了空房子,总是住着亲戚家的娃娃,只要是上学的,来者不拒,有钱就给点钱,没钱就给点粮食蔬菜,什么都不给也行,父亲和母亲从不计较。
我毕业了,父亲把家里的三个存折一共5万元存款全部交给了我,让我做生意,这是家里的全部财产。也有人问,你不担心吗?一个刚毕业的小女孩。父亲笑而不语,他眼里他的女儿身上有着比财富更让他看重的东西。
父亲做生意,从来不短斤少两,都是秤给得高高的,还要再添一些,几分几角的零钱从来不收。
这一切他知道他的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利有十分只拿七成。
父亲是城关镇西街社区的第一个万元户,父亲还是某一届靖远县的人大代表。
父亲的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父亲像大树一样承托着我们,就像土壤承托着大地——他源源不断地给予大树养分和生长的动力以及向上的精神。
云南昆明旅行,父亲讲了好多故事,我也愧疚陪伴他们太少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个个像小鸟一样羽毛丰满,离开他们,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让他跟母亲忍受孤单寂寞,我感到深深地自责。
苏芊红,女,甘肃靖远人,现居兰州。自主经营者,主营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那个酒。爱好诗歌、散文!
挚友送我雅号:三味酒屋,一曰书香,一曰酒香,一曰人情味!三味真火淬炼——不舍爱与自由!
免费起名,添加微信:000000 备注:起名!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小编 ,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762896.com/3477.html